民族
在漢語中,民族一詞具有十分豐富而复杂的內涵,可以表达多种近似而不同的概念。词汇本身歧义较多,概念和用法受到政治的较大影响,这些义项之间容易相互混淆。在不同的學科中,對於民族的範疇與用法也有許多歧異。在学术上,族群比民族的概念更宽泛。而在汉语实际使用中,民族可以被表示为包括族群、国族、民系在内的多种含义。民族一词在中英翻译时也十分容易混淆。Ethnic group和Nation经常被翻译为民族,然而更精确地应分别译为译为族群和国族。
| 人類學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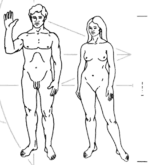 Pioneer Placque |
| 分支領域 |
| 研究方法與架構 |
| 基本概念 |
| 區域研究與次領域 |
| 相關條目 |
|
人類學史 |
民族,又称人,简称民、族。
在汉语的实际表达中,其中一种解释是,民族是血缘和文化的共同体。在中国大陆,官方一般认为民族是文化概念而不是血缘概念,然而卻將父母的民族成分作為認定公民族屬的前提。而中华民族這一概念本身较为偏向国族概念。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试图以當時漢族地區为界建立一个汉民族国家來反抗清廷的民族壓迫,此时的中华和汉族的意义等同,为族群概念。而革命党人提出五族共和后,中华民族便以此表示全中国内的所有族群,成为国族概念。
概述
概念
客觀特質來定義
只要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獨立的語言,那裡就存在著一個獨立的民族 (Wherever a separate language is found, there a separate nation exists)
——Fichte 1922, 215
如果將民族視為一個爭取政治自主性之特殊社群的這個想法,就不能不提到十八世紀的德國學者赫德(Johan Gottfried Herder,1744年–1803年)。2基本上,赫德是將民族視為一種「具有特殊性的語言和文化團體」。在十九世紀初,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年–1814年)將這個想法繼續往前推進,而主張每一個獨特的語言團體都是一個獨立的民族,要有自己的生活,也應該要控制自己的生活(Fichte 1922)。除了語言以外,本世紀的其他學者又替民族體(nationhood)的構成標準添加了很多新的客觀標準,比如說共同地域、血緣、族群、宗教、或共同信仰等等(e.g., Geertz 1963; Smith過這樣的定義:
一個民族是一個由歷史所造成的、穩定的人類社群。它是以共同語言、地域、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一個共同文化的心理機制為基礎的。
——Stalin 1994, 20 3
有些學者則否認這些客觀特質可以被用來當作定義民族的充分條件,甚至是必要條件(e.g., Canovan 1996; Gellner 1983; Hobsbawm 1992; Renan 1994)。霍布斯邦就曾經令人信服地指出,如果要對民族下一個定義的話,這些所謂的客觀條件都不是恰當的標準。以語言為例,霍布斯邦就用經驗資料告訴我們,當義大利在1860年全國統一的時候,只有2.5%的義大利人會講義大利語。此外,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時候,只有50%的法國人會講法語(Hobsbawm 1992, 60 - 61)。也就是說,所謂的民族語言(national language),基本上應當被視為民族主義實行以後的結果,而不能被視為是民族或民族主義的原因。4此外,這些用語言、族群、或者是其他的東西等來定義民族的所謂「客觀」判準,自己本身也都是會改變的、缺乏明確定義的。我們可以看葛納對於這一個觀察的論點:
把民族當成是自然天成的、上帝賜予的分類人類的方式,當成是繼承而來的、然而已經延宕許久的政治命運,其實是一種迷思。民族主義有時候會利用先前已經存在的文化,將其轉化成民族,有時候又創造出它們,往往還同時把先前存在的文化給消滅掉:這即是現實。
——Gellner 1983, 48-9
主觀意識來定義
對某些學者而言,民族的本質是主觀上的意識(subjective consciousness),而不是任何客觀上共享的特質,不論這些特質是政治上的、文化上的、或者是生物上的。賽頓-瓦特森這樣表示,「當一個社群裡面佔相當部分的人認為他們是一個民族的時候(consider themselves to form a nation),或者是表現得像他們已經是一個民族的時候(behave as if they formed one),一個民族就存在了」(Seton-Watson 1977, 5)。霍布斯邦也採取類似的立場,而將民族定義為「一群人當中,有相當比例的人認為他們是一個『民族』的成員(regard themselves as members of a “nation”)」(Hobsbawm 1992, 8)。正是在這種意義下,葛納才會一方面宣稱,是先有鬥爭,然後民族才可能隨之而來;另一方面他也強調,一個民族必須是由一群彼此認為同屬於一個民族的人所組成的(Gellner 1983, 48-9)。他這樣表示,
民族是人們的信念、忠誠、和連帶的人工產物。正因為他們彼此承認對方是同胞(recognition of each other as fellows),…… 所以他們才會變成一個民族,而不是因為其他共享的特質。…… [這種彼此間的承認]讓他們和非成員之間有了清楚的界線。
——(Gellner 1983, 7)
事實上,遠在上述這些當代的研究者指出民族的主觀建構性以前,這種觀點早就出現在一些古典社會科學研究的著作裡面了。比如說,社會學大師韋伯就強調民族體(nationhood)的互為主體面向(inter-subjective aspect),而發現到社群的所謂客觀特質,並無法用來定義民族,因為民族這個概念是屬於「價值的領域(sphere of values)」。基本上,民族這個概念在本質上就已經預設了「某些團體在別的團體之前[所擁有]的一種特別的連帶感情(a specific sentiment of solidarity)」(Weber 1958, 172)。
雷南也早在1882年就指出,所有的比如說共同的地理或地域、語言、種族或宗教等這些條件,沒有一個能夠被視為是民族存在的充分或必要條件。相反地,民族有兩個彼此相關的元素,一個是共同擁有對過去之記憶的豐富遺產(a common possession of a rich heritage of memories in the past),另一個則是要生活在一起以便傳承這些遺產的決心(a desire to live together and pass on the heritage)。因此,如果我們想要對國族的本質有進一步認識的話,我們就必須對這些由特殊歷史意識所維繫出來的連帶感(solidarity)進行探索,因為民族應當要被理解成一種道德的形式(a form of morality)(Renan 1994)。
綜合性定義
事實上,雖然上一段所提到的這種主觀元素,似乎在民族形成的過程當中確實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如果我們只用這種主觀元素來定義民族的話,則這個定義顯然是不充分的。集體連帶感可以存在於許多不同種類的社會團體當中,比如說家庭、志願團體、或者是商業組織,也都存在著這種連帶感,並不只是限於民族當中。那麼,到底民族和其他的社會團體有什麼具體的差別呢?如果要將一個擁有集體連帶感的人群稱之為民族的話,除了這個集體連帶感以外,我們還可以在這群人當中找到什麼樣的其他特質呢?主觀要素只是要將一群人視為是民族的最起碼條件而已,但是,這顯然還不是一個完整的定義。
事實上,要解答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承認這些主觀要素經常是以某些客觀要素作為基礎的。在現實生活當中,某個民族的成員,通常並不會將他們自己視為是靠集體連帶感所維繫起來的一個團體。相反地,他們會列舉一些其他的東西 --- 比如說一個共同的文化、一個共同的祖先、一個共同的歷史、共享的政治制度、或者是對於某個特定地域的從屬感,以此來將他們這些人連結在一起。
借用安德森有名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這個概念,來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對安德森而言,民族是一種人造體(artifact),是一個「想像的政治共同體(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民族是一種虛假的(fabricated)的東西,我們應該採用的策略,是用想像的風格(style),以及讓這種想像成為可能的制度(institutions),以這兩點來理解民族的特殊性。關於後者,安德森所舉的例子就是「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以及隨之而來的將國族描摹成一個社會學上共同體的新的文學文類(genre),報紙和小說(Anderson 1991)。他說,
所有的共同體,只要比成員之間有著面對面接觸[機會]的原始村落還要大,都是想像的(或許連這種村落也包括在內)。區別不同的共同體的基礎,並不是它們的虛假-真實性(falsity-genuineness),而是它們被想像的風格(the style)。
——Anderson 1991, 6
除了風格以外,我們當然也還可以找到區別共同體的其他標準,比如說它們的大小、行政組織的科層化程度、內在的平等程度等等。對研究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學者而言,我們的首要任務當然是要找出和民族相關之「想像」集體連帶感的特殊形式。卡弘所提供的下面這個清單,似乎多多少少可以視為一個共同體之所以會被想像成國族的一些可能基礎條件:
- 1. 界線(boundaries):不論是地域的,人口的,或者是兩者兼具。
- 2. 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所謂一個民族是一個整全單位(integral unit)的宣稱。
- 3. 主權(sovereignty),或至少對主權的希冀:因此和別的民族必須維持一種正式的平等關係,而且也通常維持著一種自主的、被認為是自給自足的狀態。
- 4. 合法性(legitimacy)的「上昇(ascending)」狀態:也就是說,政府必須是由大眾意志(popular will)所支持的,或至少必須是符合「人民(the people)」或「民族(the nation)」的利益。
- 5. 對於集體事務的大眾參與(participation):以民族成員之身分為基礎而被動員出來的一群人(不管是為了戰爭或是為了民間活動)。
- 6. 直接成員身分(membership):每一個個體都被理解為民族的一個緊密部份,而且和其他成員也都完全平等。
- 7. 文化(culture):包括語言、共享的信仰和價值、以及風俗習慣之實踐等的混和體。
- 8. 時間上的深度(temporal depth):民族必須是時間上的實存,包括過去和未來的世代,同時也有其歷史。
- 9. 共同祖先(descent)或种族特質。
- 10. 特殊的歷史(history),甚至是和特定地域的神聖關係。(Calhoun 1997, 4-5) 5
值得注意的是,卡弘正確地提醒我們,這些特徵只是一種民族的「修辭(rhetoric)」,是一種通常用來描述民族特徵的宣稱(claims)。事實上,我們並無法真正藉由經驗上的測量標準(empirical measures),比如說是不是能夠達成主權、是不是能夠抵擋內部的可能分裂而維持其完整性、或者是強制執行清楚的界線 來定義民族。相反地,民族通常大都是由這些宣稱所組成的,而這些宣稱不只是描述性的,同時也是規範性的。這些特徵有可能可以對民族體的感情(a sense of nationhood)提供充分的基礎,但是,沒有一個特徵是絕對需要的(Calhoun 1997, 5)。6對不同的人群而言,他們對自己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民族的宣稱,其實是建立在不同種類的事實上的。我們必須仔細地檢視所有的這些宣稱,並將這些宣稱視為是將這群人連結起來的一種信仰。因此,依循凱拉斯的建議,民族可以定義為:
一群人覺得他們自己是一個被歷史、文化、和共同祖先所連結起來的共同體。民族有「客觀」的特質,這些特質可能包括地域、語言、宗教、或共同祖先,也包括「主觀」的特質,特別是人們對其民族性(nationality)的認知和感情。
——Kellas 1991, 2
馬克思主義意義下的「民族」
馬克思去世之後,恩格斯在1884年所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被視為馬克思主義民族學的第一本經典著作。提到了民族形成的規律。人結合成群;由血緣關係組成原始的家庭型式並形成親屬制度,逐漸排除同胞的性交關係;共祖的血族團體結成氏族,氏族結成部落,進而結成部落聯盟,融合成「民族(Volk)」;隨著生產力的增加,分工擴大,新的生產關係出現,新階級產生,使得氏族制度漸漸不能負荷而消滅,隨之產生由「新民族(Nation)」組成的國家。
從氏族到國家,「民族」的用法有兩種;前一種是相應著血緣關係而使用的「volk」,後一種則是充滿著現代「民族」國家意味的「nation」。也就是說,恩格斯在提到民族的發展規律時,所指的現代的民族或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民族,應該是相應著現代國家逐漸成形,涉及到以國家意識為核心的人們共同體所構成的「國族(nation)」。這個詞必須依附於「國家」形成的論述脈絡,才有它的地位的。
民族既然依附於國家體制的產生,相應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是特定歷史發展階段中的一個產物。等到國家體制所服務的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壓迫出現之後,《共產黨宣言》中所謂「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就讓位給了階級利益;在階級對立中,只要能消滅最基本壓迫型式的階級壓迫,其他型式的壓迫(包括民族壓迫)就會隨之解決。等到那個時候,民族將會像國家一樣,失去存在的必要而自然消亡。
1912年,時任真理報編輯的史達林,為了解決第二國際及俄共內部對民族自治、民族自決的爭議,被列寧派到維也納去寫民族問題的小冊子。其成果就是被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引為「民族」定義聖經的《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從現代的民族研究看起來,這個定義是相當粗糙的。然而,史達林從歷史唯物論的角度,以明確的客觀特徵首次為「民族」提出了定義:
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 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 的穩定的共同體。
民族也和任何歷史現象一樣,是受變化法則支配的,它有自己的歷史,有自己的始末。......只有一切特徵都具備才算是一個民族。
民族不是普通的歷史範疇,而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範疇。
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即引史達林定義的這四項民族特徵,為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進行民族識別和民族認定。
200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民族的定義[4]: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血統視為認定公民的民族成份的大前提[5]。
研究
在過去的兩百年當中,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在形塑世界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遠比比如說自由或者民主等其他的思想要強大的多。在二十世紀初期,英國的公眾人物諾曼·安吉爾就曾經戲劇性地論道,「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歐洲人而言,政治民族主義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東西,不但比人道精神、禮節、慷慨、同情更重要,甚至於比自己的生命本身都還重要」[6]。
然而,關於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定義到底是什麼,相關內容應該是什麼,在歷史上又曾經有過什麼變化,卻一直是相關學者爭論不休的問題。多數的學者都同意,民族主義是一種自決的政治主張(political doctrine of self-determination)。但是,到底什麼樣的人類集團可以被授與這種自決的權利,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可以宣稱這種自決的權利,卻一直是一個爭辯中的問題。當試著要替民族主義下一個定義的時候,德國學者亞特就無奈地表示,「在當今的政治分析的詞彙當中,民族主義是最混淆的一個概念之一」[7]。凱克門諾必克也這樣宣稱,「不論是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學家、或者是心理學家,沒有兩位學者用同樣的方式來定義民族主義」[8]。
相關學者之所以會有這種無法對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基本定義產生共識的局面,幾個可能的原因。
高度的政治意涵
一個最根本的原因,當然是這些語彙充滿了高度的政治意涵[9]。葛納就曾經這樣表示,「理論上研究民族主義最困難的地方,就在於我們必須在視民族主義為『民族的(national)』和『自然的(natural)』的虛假解釋 --- 通常它們都只是虛構出來正當化民族主義的 --- 以及視民族主義為受到時間和脈絡制約的真正解釋之間,做一個清楚的劃分」[10]。
儘管葛納強調區辨「民族主義宣傳」和「民族主義研究」,但是民族主義的研究卻在本質上和知識的實踐脫離不了關係。正如詹姆士指出:
- 所有從事民族主義研究的人,在「定義」上就已經是在從事一種知識的實踐了。即使你是有意識地坐在平靜的研究室中和政治運動者相互隔離,你的研究成果卻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到你的研究對象,和這個民族主義運動相關的每一個活生生的人。
- 從民族主義過去的發展歷史來看,文化菁英-尤其是社會科學的工作者,一直都處在民族主義風暴的最前線。無論是官方版的民族主義,或者是反對運動的民族主義,幾乎都是透過知識份子在意識型態上掌旗和操盤。
- 自從民族主義在19世紀末開始襲捲整個世界以來,透過國家機器所掌控之教育體系的運作,知識份子一直都在「民族文化」的生產和複製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1]。
複雜性和多重性
研究民族主義的第二個難題在於它所涉及之經驗現象的複雜性(complexity)和多重性(multiformity)[12]。事實上,我們常常將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空間裡面所發生的不同形式之經驗現象,一律統稱為「民族主義」。比如說,不論是不列坦尼的分離運動、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甚至是宣稱要為中國的未來奮鬥不懈的1989年中國學生示威活動,通通被同一個標籤“民族主義”所概括,雖然這三者不但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路徑,也發生於完全不同的政治社會結構當中。因此,亞特就曾經指出:
事實已經清楚地擺在眼前,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涵蓋多種情形的標籤以及正當性來源,本身就隱藏了極度的矛盾。它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解放,但同時卻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壓迫。就此而言,民族主義是一個同時存放著危險和機會的地方。如果我們要宣稱這個詞彙真正代表什麼、或者應該指涉什麼的話,我們一定要將具體的歷史脈絡指陳出來。或許我們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初步結論,民族主義並不是只有一種形式,而是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說,我們應該用複數,而不是單數,來描摹這個詞彙[13]。
跨學科本質
民族主義研究的第三個難題在於它的跨學科本質(interdisciplinarity)[14]。最早研究這個領域的是歷史學者,但是,由於和民族相關之經驗現象的多重性和變異性,人類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社會心理學家、語言學家、國際關係學者、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領域的學者,也都陸續加入了民族主義研究的行列。
英國社會學者安東尼·D·史密斯就曾經表示,和民族主義研究相關的題目至少包括以下這些子題等[15]:
- 族群(ethnicity)的起源和形成
- 造成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相關條件
- 族群社群(ethnic community)的本質
- 族群認同的性質
- 民族(nation)的起源和形成
- 民族認同的本質
- 民族的社會、政治、文化基礎
- 民族和現代性(modernity)的關聯
- 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和民族運動在性別、階級、以及文化上等面向所展現出來的特質
- 民族主義知識份子(nationalist intellectuals)在民族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 世界上現有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在文化和社會層次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 民族和民族主義對地緣政治(geopolitics)所造成的影響
某一個學術領域的學者通常只能探觸到這些現象的某一部分而已。如果要對民族主義這個經驗現象有比較完整的掌握的話,一個跨學科取向的研究設計可能會是一個無法避免的結果。
方法論上的困難
當把像民族或民族主義這樣的概念放在一般社會科學研究的因果關係模型中的時候,無可避免地會遭遇到很多方法論上的困難。比如說,在分析民族主義的起源的時候,就會發現到,在很多時候,民族主義同時扮演著原因和結果的角色。寇克力(Coakley)就曾經這樣表示:「民族主義微妙的地方,就在於其因果關係十分地難以決定。民族主義自己本來就是難以捉摸的(amorphous),而它不但對其他的社會現象有影響力,而且自己又[同時也]是這些社會現象的結果」[16]。
民族是某一類型的團體(group),這一點大致上是沒有問題的。
註釋
1. 關於「nation」這個詞彙應當如何翻譯成中文的討論,可以參考陳光興(1994,163-4);黃昭堂(1994,202-3);浦薛鳳(1963,166-73);以及朱浤源(1988,118-25)。
2. 關於赫德和民族主義相關的重要作品,可以參考Herder (1969, 1992)。至於和赫德相關的研究,可以參考Ergang (1966)。
3. 原文最早發表於1912年。
4. 霍布斯邦這樣表示,「民族語言因此幾乎都是半人工的建構物(semi-artificial constructs),在某些例子中,比如說現代的希伯來語(modern Hebrew),它根本就是完全被發明出來的」。因此,「它們[這些民族語言]剛好和民族主義迷思所宣稱的相反,它們並不是民族文化的原生基礎,也不是民族心靈的產物」(Hobsbawm 1992, 54)。
5. 當然,這份清單並不是「最後」的清單。如果我們願意的話,我們還可以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元素。卡弘自己就這樣表示,「[事實上]並不存在一份完美的清單。我們所感興趣的是民族的共同模式,而不是提供一個對民族的正確定義。[在這份清單所]舉出來的這些例子,可以幫助我們發展出一個『理想型』,但是,這只是一種對於概念化過程的助力,而不是一個操作定義,或者是一個經驗上可以驗證的描述」(Calhoun 1997, 5)。
6. 就這一點而言,所謂世界上大多數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都不是「純粹的民族」這種講法,其實是沒有太大意義的。畢竟,民族國家本身就是一個意識型態的建構,是民族主義教條的產物。
參考文獻
英文書目
- Alter, Peter. 1994. Nationalism. 2nd ed.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Edward Arnold. New York: Edward Arnold.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 London: Verso.
- Calhoun, Craig. 1997.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anovan, Margaret. 1996. Nationhood and Political Theory. Cheltenham, United Kingdom: Edward Elgar.
- Ergang, Robert Reinhold. 1966. Herder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erman Nationalism. New York: Octagon.
- Fichte, Johann Gottlieb. 1922.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translated by Reginald Foy Jones, and George Henry Turnbull. Chicago: Open Court.
- Geertz, Clifford. 1963.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edited by Clifford Geertz, 105-57.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ellner, Ernest. 1964. Thought and Chang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ladney, Dru C. 1997. Ethnic Identity in China: 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Greenfeld, Liah.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iffiths, Stephen Iwan. 1993.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Threats to European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rder, Johan Gottfried. 1969. J.G. Herder on Social and Political Culture. translated,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rederick M. Barnar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bsbawm, Eric J. 1992.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mes, Paul. 1996. Nation Form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Abstract Community.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 Kecmanovic, Dusan. 1996. The Mass Psychology of Ethnonationalism. New York: Plenum Press.
- Kellas, James G. 1991.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McKim, Robert, and Jeff McMahan. eds. 1997. The Moralit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nan, Ernest. 1994. Qu'est-ce qu'une nation? In Nationalism, edited by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D. Smith, 17-1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eton-Watson, Hugh. 1977. Nations and States. London: Methuen.
- Smith, Anthony D.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 Smith, Anthony D. 1998. 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 A Critical Survey of Recent Theories of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 Snyder, Louis L. 1990. Encyclopedia of Nationalism. London: St. James Press.
- Stalin, Joseph. 1994. The Nation. In Nationalism, edited by John Hutchinson, and Anthony D. Smith, 18-2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ax. 1958.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lated,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ns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文書目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陳光興,1994,帝國之眼:「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17:149-222。
- 陳奕麟,1999,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認同之曖昧不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3:103-31。
- 黃昭堂,1994,戰後台灣獨立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見施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頁195-227。台北:前衛。
-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
- 浦薛鳳,1963,現代西洋政治思潮。台北:正中書局。
- 沈松橋,1997,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和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28 :1-77。
- 朱浤源,1988,從民族到國家:論Nation意義的蛻變 。中山社會科學譯叢 3:118-32。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1972。北京:人民出版社。(恩格斯「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
-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編,《斯大林全集》第二卷,1953。北京:人民出版社。(史達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 江宜樺. . 台北: 揚智文化. 1998. ISBN 957-8446-66-7.
- 王柯:〈「民族」,一个來自日本的誤會〉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2003)
- 邸永君. . 民族研究. 2004, (3): 98–99.
- 茹莹. . 世界民族. 2001, (6): 1.
- 周星 民族學新論 1992年 第1版
- . [2018-03-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3-06).
- 公民民族成份满18周岁后两年内可申请变更一次
- 引自Snyder 1990, vii
- Alter 1994,1
- Kecmanovic 1996,15
- e.g., McKim and McMahan 1997, 156-7; Smith 1998, 223
- Gellner 1964,151
- James 1996,193
- e.g., Calhoun 1997, 20-2; Canovan 1996, 50; Smith 1998, 223
- Alter 1994, 2
- e.g., Griffiths 1993, 11; Hobsbawm 1992, 10; Kellas 1991, 1
- Smith 1998,222
- 引自Kecmanovic 1996, 211
